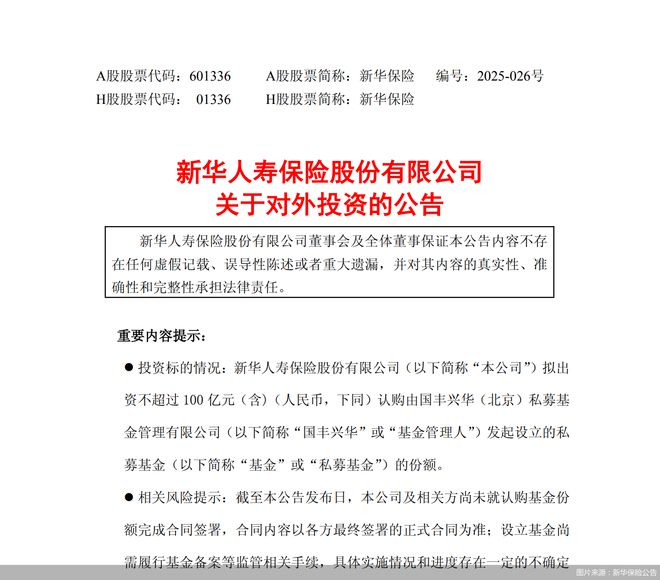原题:用青春热忱叩开“冷门绝学”之门
—— 走近三位选择“无用之用”的年轻人
在时光的褶皱里,总有一群年轻人选择与“冷门”为伴——他们在故纸堆中叩问民族交融的脉络,在显微镜下延续器物跳动的脉搏,在甲骨金文中追问文明的起源。在五四青年节前夕,我们走近3位冷门学科的江苏青年学人,探寻这些选择“无用之用”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。
为千年帛书注入青春力量
2024年夏,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(修订本)》的出版,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张婷的书桌上投下一束历史的光。这位出生于1995年的成都姑娘,用3年时间在帛书残卷中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,将埋藏两千年的智慧重新缀合成篇。
震惊世界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中,三号墓出土的12万字帛书尤具传奇色彩。这些深埋地下的典籍涉及政治、军事、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医学等诸多领域,堪称西汉早期的“地下图书馆”。其中,《五星占》刷新了世界天文学史认知,《五十二病方》改写了中国医学史,而张婷专注的《阴阳五行》甲篇则另有玄机。
在三号墓所出帛书中数术类文献占有很大比例,《阴阳五行》甲篇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。“通俗地说,这类文献有点类似于后世占日择吉的‘历书’,但又有所不同。”张婷说,三号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子、军事将领利豨。《阴阳五行》甲乙篇等兵占书应该是墓主人自编自用的军事参考书,反映的是这位将军生前的作战活动,其中一些占卜内容会根据具体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整,可与史书互证,提供了一些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史实。
“当年细读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《文字学概要》,没想到后来能够有机会参与先生带队的马王堆帛书修订工程。”张婷轻抚案头泛黄的讲义,回忆求学轨迹时,眼中闪动着热忱。从复旦大学硕士阶段初探帛书奥秘,到如今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程少轩教授指导下深度参与“简帛阴阳五行类文献集成及综合研究”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冷门绝学项目,这个痴迷古文字的女孩,在布满裂痕的帛片间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。
帛书整理堪称出土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“显微手术”,工作看似枯燥乏味,张婷却乐在其中。她告诉记者,马王堆帛书出土前长期泡在水中,相互粘连,破损严重,很多字无法辨识。帛书又是以折叠的方式放置,对折的页面出现大量印文,有些甚至渗印到其他帛书上。“这就需要我们对帛书进行拼缀和复原。首先将帛书原件进行拍照和红外扫描,然后再借助电脑绘图软件进行水平翻转或镜像翻转,确定每一块残片的位置,恢复帛书的原貌。”在张婷看来,这样的过程好似玩“拼图游戏”,难度显而易见,但也蕴藏着无穷乐趣。
在程少轩教授指导下,她不但通过修订基本复原了《阴阳五行》甲篇文本,还撰写了《马王堆帛书〈阴阳五行〉甲篇〈刑日〉章“刑日”推算方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等论文,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(修订本)》中《阴阳五行》甲篇一篇则是以其硕士学位论文《马王堆帛书〈阴阳五行〉甲篇校释及相关问题研究》为底本写就。这篇论文也被收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《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》大型丛书中,即将出版。
“从马王堆汉墓发掘至今,帛书整理已经历五十年,五代学人参与其间,薪火相传。”作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第五代团队中的一名年轻成员,张婷很荣幸成为这项事业中的一名“接棒人”,为这座“汉代图书馆”注入青春力量。
与时光对话的文物医生
午后,苏州澹台湖畔的吴文化博物馆内,95后马鸣远换上印着馆徽的白大褂,轻轻推开修复室的门。阳光从侧窗斜斜洒入,照在案台上未完成的书画残卷上,细碎的尘埃在光束中浮动,仿佛被时光凝固的颗粒——这里是他的“手术室”,作为一位书画文物修复师,每一件文物对他来说都是一位沉睡的病人,而他,是那位用指尖唤醒历史的医者。
6年前,马鸣远还是考古专业的学生。田野实习中,他第一次触摸到深埋地下的文物,在博物馆实习时又目睹了文物修复师如何让破损的古画重焕光彩。那些时刻,他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联结——残破的书画背后,藏着被岁月掩埋的故事,而修复师的手,恰是揭开这些故事的钥匙。2019年,他循着招聘启事来到苏州,从此与吴文化博物馆的古字画结下不解之缘。
修复室的工作台前,马鸣远常觉得自己在演绎一场无声的独幕剧。他习惯先凝视昨日修复的书画,观察胶矾水是否渗透均匀,或是掂量瓷钵中糨糊的余量。案头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步骤:某幅扇面需补全虫蛀缺口,某张绢本画要调整托纸的湿度。动作起落间,他总想起师傅的叮嘱——“手腕摆动,幅度要大”。传统书画修复的“洗揭补全”四法,看似简单,却需经年累月的体悟。淋洗画心时,水流从浑浊到清澈的微妙变化,全色时颜料与古纸的色差弥合,皆在毫厘之间。他笑称自己常陷入“脑中演练千百遍,手下动作仍生涩”的窘境,但正是这份笨拙的虔诚,让他逐渐触摸到技艺的精髓。
科技悄然改变着老行当的节奏。过去判断清洗是否彻底,全凭水流是否透明;如今用pH值试纸一测便知。色度仪取代了肉眼比对的模糊,显微镜下纸张纤维的走向清晰可辨。但马鸣远仍固执地保留着某些传统:调配染纸时,指尖摩挲纸张的触感;全色时屏息凝神的专注。他说,科技是理性的尺,而修复师的心,才是感性的秤。修复书画时,他遵循“远观一致,近观有别”的原则——既不让残缺破坏文物的整体气韵,又为后人留下辨别的痕迹。这种平衡,恰似与历史签订的契约:敬畏原貌,亦不回避当下的介入。
最惊心动魄的,莫过于“揭命纸”的时刻。某次处理扇面时,覆背纸与画心几乎融为一体,稍有不慎便会撕裂绢帛。空气湿度计就摆在手边,他却觉得连呼吸都可能打破脆弱的平衡。当羊毛排刷的旧痕从命纸间显露时,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正与数百年前的装裱师隔空对话——前人补洞的粗疏,折条排列的缜密,甚至刷毛残留的多少,都成了破译往事的密码。这种跨越时空的触碰,让他想起兵马俑修复者发现的秦代陶工指纹,“原来我们都在完成一场接力”。
谈及行业,马鸣远不讳言书画修复讲究师徒相授,而书画修补必须耐住寂寞。但他也看到希望:报考文博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多,公众对修复工作的关注度持续升温。他记得某次展出修复完成的草鞋山遗址陶器时,有位老人盯着展柜良久,喃喃道:“这东西和我小时候家里摔破的碗好像。”那一刻,他确信自己的工作不只是拯救器物,更是缝合文明的断层。
解读“死语言”为文化戍边
2019年,吴昌连考入南京大学,在元史研究室攻读中国民族史硕士学位,专注于清代北方民族史研究。要深入研究这一领域,需要学习满文,然而,掌握这一语言并非易事。
满文作为一种濒临消亡的文字,除极少数专家学者之外,绝大多数人已无法识读或理解其内容。研一上学期,南大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开设“满文史籍研读”课,吴昌连立即报名。“特木勒老师教满文有一套成熟高效的方法,先教字母,然后直接读满文档案。每名学生课前会领取一份满文档案,完成拉丁转写、单词释义、文段翻译作业,然后在课上汇报,特木勒老师会适时讲解里面的语法等问题。”吴昌连说。
课程刚开始时,吴昌连水平有限,有些满文词汇识读不出,语法问题也不懂,也不好总请教老师和学长,于是他加入了一个满语学习QQ群,通过不断向高手请教,他弄清了困扰他良久的语法问题,为了弄清《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》里出现的“奏蒙古事侍卫”这一官职名,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抄了一个月的满文档案……通过硕士期间不间断的学习,他逐渐掌握了这一冷门语言。
2022年9月,吴昌连继续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特木勒教授。一晃又是三年过去,现在已博士三年级的吴昌连每天在宿舍里写毕业论文,过着宿舍往返食堂的两点一线的生活。虽然他已不再花整块时间学习满文,但每天都会与满文史料“见面”,并且凭借自己掌握的满文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。比如,吴昌连曾注意到,一些清朝民人曾生活在准噶尔部。这些卑微的小人物,在官修史书和文人著述中难觅踪迹,但满文奏折里却记载了他们的出身和经历,最终吴昌连依靠这些满文史料撰写出论文《平定准噶尔战争中部分清朝民人俘虏的命运轨迹》,发表在《军事历史研究》上。
运用多语种史料解决学术难题是南大元史研究室的强项。硕士生期间,吴昌连又学习了波斯文,用于研读波斯文史籍《巴达克山史》,这帮他佐证了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清廷颁给巴达克山的敕谕内容。
无论满文还是边疆民族研究,吴昌连坦言都有些“冷”。“但这类学科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和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吴昌连说,从“中央大学”时代的边疆政治系到南大元史研究室,再到如今的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,这一学术传承充分彰显了冷门绝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意义。古文字、边疆史地等冷门绝学中的研究成果,往往能够在南海主权归属争端等攸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中,提供事实依据、澄清历史争议。无论是对内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一致性,还是对外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、各民族多元一体、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,讲好中国故事,冷门绝学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冷门绝学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,而是与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重要学术资源。“我们需要从学科体系建设、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,对冷门绝学给予更多的重视与支持。”吴昌连说。
原创文章,作者:Admin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camerich.net/archives/2737.html